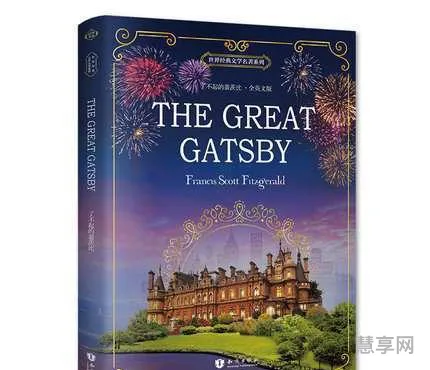盖茨比为什么了不起(盖茨比的伟大之处在哪)
盖茨比为什么了不起
这得结合时代背景看。盖茨比所在的时代是1921——1925年,那时候的美国处于一战结束,各种清*的戒律在这个时候也被冲破,楼房越建越高,股市的数字也越来越大,女权运动开始兴起,但人的道德底线却在逐渐滑坡,柯立芝总统实行的禁酒令起了反作用,享乐主义、拜金主义的思想开始流行。而以汤姆•布坎南为代表的旧贵族们可以继承来自父母的大笔遗产,另外这些旧贵族特别风流,过着奢靡生活。
菲茨杰拉德往往被视为“垮掉的一代”的*代言,但垮掉的又岂止是一代人?触目所及,如果有心,何处不是苍夷沉珂?正如菲茨杰拉德所言,所有的人生都是一个垮掉的过程,人生有时必须在“努力无用”和“务必奋斗”这两种感觉之间保持平衡,甚至“明明相信失败在所难免,却又决心非成功不可”“‘自我’就会像一支箭一样,不停地从虚无射向虚无,这股力量是如此之大,唯有重力才能让它最终落地。”

也正因此,“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”的盖茨比自有其“了不起”之处,他不仅代表了新世界美国梦的兴起与倾颓,更展现了人性中关于希望的浪漫期待。他不仅慰藉不同时代里忧伤依旧的年轻人,也展现出其美国式*(甚至可以说是人类乐观而天真那一级)的核心所在:他对于“黄金女郎”黛西的勇敢追求,不仅触及爵士时代集体情感,也挠到这个民族的痒处,一往无前,无知无畏。
合情合理的悲剧最令人扼腕叹息,一步步看起来不得不走,到头来却都是谬误,对命运的抗击与失落的虚空同存,理想的幻灭与永恒的希望对映,这也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力量所在。虽然我上篇说从情感层面讲黛西衬不起盖茨比的深情,但盖茨比对黛西的追求也超越情感而是一种理想,其伟大也不因黛西的不登对而付之阙如。
事实上,不仅是在《挪威的森林》向菲茨杰拉德致敬,村上春树第一部*作《且听风吟》中就有闪现菲兹杰拉德的身影。至于村上春树本人,他是菲茨杰拉德作品的日本译者之一,评价菲茨杰拉德应该有发言权。他认为菲茨杰拉德本人,“不妨说是美国这个国家青春期激烈而美丽的表露”,至于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,他认为小说魅力不仅在于其“毁灭的美学”,更在于“拯救的确信”。
盖茨比的伟大之处在哪
我很欣赏这一判断。谈到拯救,就不能不说小说中作为希望象征的数次出现的“绿灯”。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也有别的译名,《大亨小传》被吐槽,《灯绿梦渺》少人知道,其实想想来看,“绿灯”确实在盖茨比的梦想中占据了很高地位。
当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结尾,叙述者尼克离开盖茨比别墅的最后一个晚上,不仅感受到盖茨比对于“绿灯”的期待,也总结了其不可避免的悲剧性,“他(盖茨比)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,他的梦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,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。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,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饨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,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。”
萧条异代不同时。虚无之中,无处皈依的“自我”何处安放?即使对于小说是否高估有不同评价(譬如在我个人名单里,这肯定不是第一流的杰作之列),尽管如此,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在文学史上应该有其相应的地位。
小说之中,盖茨比怎么能够不爱黛西,也正如黛西不会选择盖茨比一样,“太正常了”,而在现实之中,童话经不起成人世界的物换星移,菲茨杰拉德和妻子珊尔达未能曲终人合,也几乎是必然。
“黛西”可以一个隐喻,无论是小说中的女神还是生活中的娇妻,无论是否值得,无论是否得到,最终恐怕难逃毁减与幻灭,就像菲茨杰拉德晚期的喃喃自语“在灵魂的真正的黑夜里,日复一日,永远是凌晨三点钟”。毕竟,长的是人生,短的是梦想,但是支撑人生的,就是那盏似有若有的“绿灯”,真假不计。
了不起的盖茨比经典语录
盖茨比并不是完人,发家可疑,所爱非人,但小说中旁人对于盖茨比两个最常见的指控,一个没去过牛津大学,以及杀过人(包括最后开车撞死茉特尔.威尔逊),恰恰都不存在,而他身后事的寂寥,那些从他聚会中汲取欢乐的人反映的“不痛不痒、无关紧要”,更是反衬毁灭的残酷。
盖茨没见到黛西时,只能隔着幽暗的海水奋力触摸黛西家门口的那盏绿灯,等他再见黛西时,那盏灯的巨大意义消失了,“神奇的宝物已经减少了一件”,又等到一切因死亡与叛变而尘埃落定时候,绿灯又出现了,“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,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。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,不过那没关系——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,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”
这里的“绿灯”,令我不禁想到侯麦*《绿光》的传说,“谁能看到绿光,谁就能得到幸福”,简直类似宗教意义上的寻找圣杯,不过这里的宗教情感却又是个人而世俗的,因而也在各个时代,赢得共鸣。